| 志愿军第13兵团主力部队分别从安东、长甸河口、集安三地跨过鸭绿江。 没有人知道前方山谷里埋伏着怎样的火力网,但所有人都清楚,新中国第一次出国作战,只能胜,不能败。 入朝前,毛主席在致彭德怀、邓华的电报中反复强调“我军第一仗必须力争胜利”。 彭德怀在师以上干部动员会上也提醒各级指挥员:“第一仗打不好,就会影响士气、影响大局。” 
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了各级指挥员的意识里,也为随后几次战役中“火线撤职”的雷霆手段埋下了伏笔。 第二次战役打响时,志愿军司令部要求东线九兵团兼程迂回长津湖,西线十三兵团则派四十二军一二四师穿插顺川、肃川,关门打狗。 军情火急,兵团电报里连用“星夜兼程”、“不得迟误”等措辞催促,可一二四师政委季铁中却在抵达大同江边时下令部队停止架桥。 理由是侧翼一二五师尚未赶到,如果孤军渡江,背水遇敌,将陷全师于绝境。 师长苏克之急得直跺脚,却拗不过政委的“最后否决权”。 这是红军时期留下的老规矩:军事行动一旦政委不同意,就不能干。 但是,其实早在抗日时期,毛主席就修改了这一制度。政委的“最后否决权”只能用于政治领域,而不能用于军事行动。 无奈季铁中资历深厚,师党委最终还采用了“老办法”处理。 于是千军万马在江边蜷伏了十几个小时,给了美军撤退的时间。 第二天拂晓,电台里传来了兵团严厉的批评:“延误战机,按级追责。” 战役总结会上,彭德怀只丢下一句话:“政治工作要保证打仗,不是拖延打仗。” 
最终,季铁中因“违背现行指挥原则”被当场撤职,赶回后方。 几乎同一刻,东线长津湖的雪下得更大。 二十六军八十八师受命抢占独秀峰,掐住美军突围的瓶颈。 师长吴大林和政委龚杰摊开地图,发现要穿过四十公里的峡谷,而向导只剩一位朝鲜老汉,夜里零下三十五度,大雪封山,迷路就意味着整师冻僵。 两人商量再三,决定等天亮再动身。 翌日清晨,美机像嗅到血腥的秃鹫,沿着山沟反复俯冲,部队被炸得七零八落,等他们冲上独秀峰,比预定时间晚了十五个小时,陆战一师已撕开缺口南逃。 宋时轮在电话里怒吼:“这是怯战!” 一句话,吴大林和龚杰被同时撸掉职务。 转眼来到第五次战役,志愿军把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,可粮弹告罄、援敌反扑,全军转人撤退。 六十三军一八九师奉命在临津江南岸阻击,掩护兄弟兵团后收。 师长许诚看着地图上一道又一道蓝箭头,迟迟下不了决心渡江。 政委蔡长元提醒他,再晚,江岔子就被敌机炸塌,可许诚仍想等工兵架好浮桥再过。 结果部队拖到午后才分批下水,刚爬上滩头,美二十五师便集中飞机坦克狂轰滥炸,两个后续军被堵在北岸,眼睁睁看着炮火把江面撕成碎片。 彭德怀在空寺洞指挥所拍案而起:“师长犹豫,贻误全局,就地免职!”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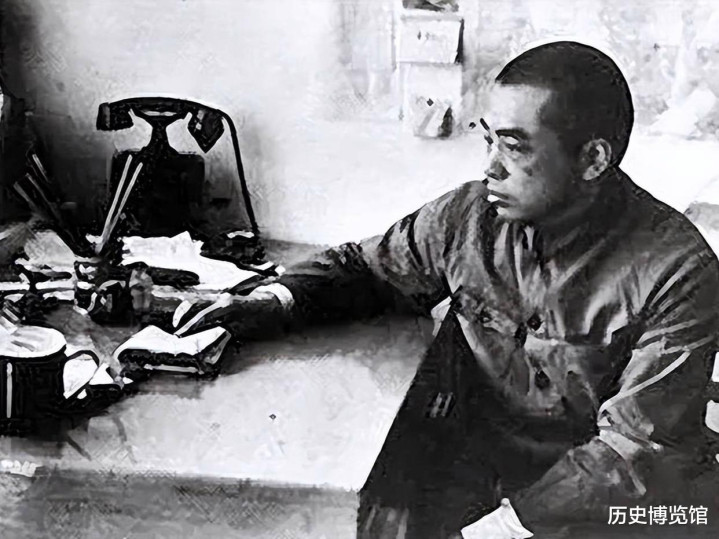
更惨痛的悲剧发生在六十军一八○师。 五月下旬,该师陷入美军七师、二十四师及韩军多路合围,电台失灵、粮弹尽绝。 代师长郑其贵本想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,可各团报告“四面都是坦克灯”,于是他下令“分散突围”,把整师拆成无数小股,钻沟越岭。 结果三千多人倒在深山,三千多人走进战俘营。 消息传到北京,周恩来深夜召集军委会议,连说三句“惨痛!” 郑其贵也被撤职、审查。 五位师级干部被就地撤职,那么他们之后的仕途又是否有受到影响呢? 季铁中回东北后,被留在沈阳,办起了政治文化干校,1955年授大校,没耽误; 吴大林、龚杰同样戴大校肩章,一个镇守辽西,一个镇守苏南; 许诚先授大校,1964年再扛一颗星,晋为少将,官至天津市委书记; 唯独郑其贵1955年只拿到上校,直到1963年才晋升大校,行政职务也止步副师。 晚年,郑其贵拖着肺气肿的病体,给一八○师牺牲官兵的家属写信,每写一封,就在笔记本上画一个“○”,说是“替他们团圆”。 今天,当人们在军事博物馆看见那些被炮火撕碎的军旗,也许仍能闻到长津湖的冰碴味、临津江的血腥味,更能触摸到一种滚烫的逻辑:胜利从来不是无代价的,而真正的勇敢,是在代价面前仍然选择向前。
|

